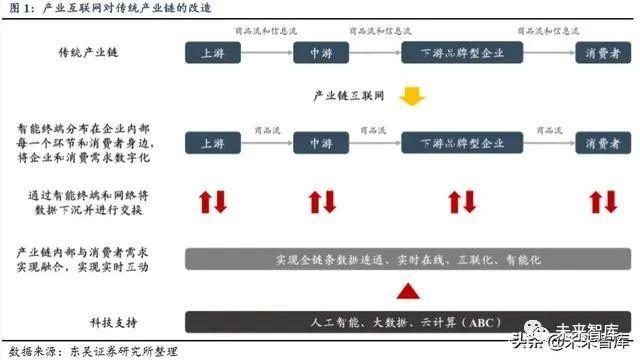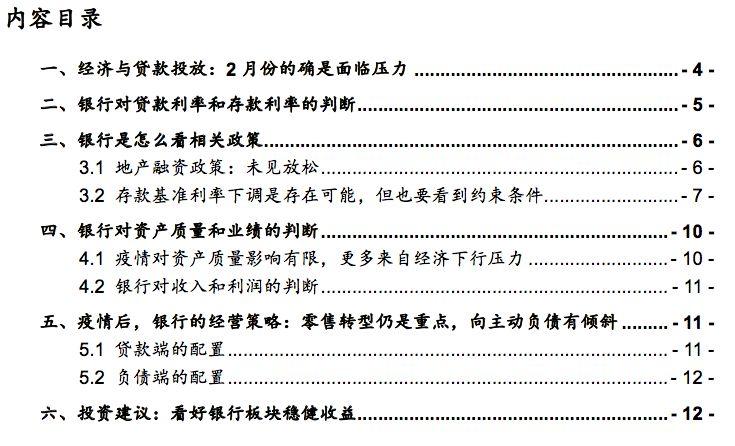作者:聂静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草原丝绸之路”(以下简称“草原丝路”)这一概念自出现以来,使用者众多,但对于其含义和具体路线的认识却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导致有学者质疑其命名的科学性。反对者的意见主要有三点:第一,“丝绸之路”得名于该商路上的大宗货物丝绸,而历史上所谓“草原丝路”主要以茶马贸易为大宗,名不副实;第二,在特定时空框架下,由于丝绸之路沙漠—绿洲路段与草原路段存在交集进而形成丝路网络,因此不应将两个路段分割开来;第三,单从草原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称呼这条国际化商路,不够科学。笔者认为上述理由有失偏颇,“草原丝路”由“丝绸之路”派生而来,“草原丝路”被冠以“草原”之名,恰恰精准地体现了该路段的特色,这一概念的科学性毋庸置疑。

“丝绸之路”别名众多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此概念的首创者为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初专指汉代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及印度之间以丝绸为主的贸易通道。20世纪初,德国东方学学者赫尔曼沿用“丝路”概念,述及具体线路时,进一步从中亚、南亚延伸到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岸的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发起丝路探险热潮,他们在游记或研究著作中普遍使用“丝绸之路”这一称谓。“丝路”概念由此得以确立,具体线路指古代中国经西域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通路线,此即后世所谓的“狭义丝绸之路”概念。“丝路”概念由狭义向广义转化,由起初对丝路干线的粗浅认识,到后来的细微掌握,归因于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丝路研究热潮的推动。到20世纪末,出现了“广义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凡经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局限于陆路,包括海路在内,可以一概称为“丝绸之路”。
拓向广义的“丝路”概念,又衍生出多个新称谓。除经海路西行的线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之外,“狭义丝绸之路”即经西域西行的路段,被称为“沙漠—绿洲丝路”;经欧亚草原西行的路段被称为“草原丝路”,其中从中国内地通往贝加尔湖的这段路线被称为“瀚海路”;经四川、云南入缅甸、印度的线路(川滇缅印通道)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路”。这些称谓都是以地域或地貌特点来命名的。上述诸多“丝路”中,只有“沙漠—绿洲丝路”属于“狭义丝绸之路”范畴,而“海上丝路”、“草原丝路”和“西南丝路”等均属于“广义丝绸之路”范畴。
随着丝路研究内容的进一步细化,还出现了以不同历史时期各主要通道上的大宗或有代表性的货物为各条线路命名的方法,如早期陆上丝绸之路(实指沙漠—绿洲丝路)被称为“玉石之路”;“草原丝路”被称为“皮毛之路”或“茶叶之路”;“西南丝路”被称为“茶马古道”;“海上丝绸之路”被称为“瓷器之路”或“香丝之路”。
这些名称表面上与早期丝绸之路概念的内涵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大多属于“一路多名”,其中有的则是干线与支线的差别,都是丝路概念外延由狭及广的产物,是研究与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每个称谓皆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旧名重提,还是当代新创,具体所指交通线路及其变迁情况如何,应当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提法,究其本质,历史上丝路曾是连接欧亚非的贸易要道,主干明晰,支线众多,古往今来,不同历史时期,各路段受政治、军事等社会因素以及地理环境变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或畅通无阻,或时断时续,或遭废弃,或另辟蹊径。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传递的都是东西方交通生生不息的联系,也昭示着人类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东西方的重要交通路线,不仅发挥其贸易功能,还与沿途各国政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民族迁徙与融合等密切相关,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多重历史文化内涵。
“草原丝路”得名综合地貌等多项特征
“草原丝路”亦称“皮毛之路”或“茶叶之路”,指历史上从中原出发向北至漠北蒙古草原折而西行,再经欧亚草原地带直达欧洲的交通道路,因古代中国丝绸、茶马、皮毛制品等货物多经草原游牧民族运销到西方而得名。此路应为狭义丝绸之路(陆上丝路)的组成部分。具体路线由中原出发,可分数条路线北上进入蒙古草原,抵达蒙古高原后线路一分为二:继续北行可达今贝加尔湖(古称瀚海),由此折而向西穿越西西伯利亚草原(大体沿着今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线)抵达东欧;或由蒙古高原中心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向西越杭爱山,沿阿尔泰山西行,再折向南进入天山山脉以北草原,沿天山北麓至伊犁河,过碎叶川、塔拉斯河,西行经锡尔河,沿河而下至咸海,再渡乌拉尔河、伏尔加河,直至黑海北岸。
探究“草原丝路”得名依据,首先,从地缘因素来考量,此路名显然源于对地貌特征的概括,绝非如有学者所言仅仅出于草原游牧民族角度。如前所述,草原丝路干线主要途经欧亚草原地带,是其得名的缘由。该路段经行途中也有非草原景观的荒漠和半荒漠地貌类型,但我们应该关注主体。自中原地区先北行再折而西行的草原丝路,横贯整个欧亚草原,欧亚草原东西延伸呈连续带状分布,西起多瑙河下游,向东依次为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哈萨克丘陵、蒙古高原,直至中国东北松辽平原,东西绵延近110个经度,是地球上最宽广的草原带,在地形和地貌上堪称畅通无阻的天然通衢,为东西方交通提供便利。草原丝路主干线分布于北纬40—50度之间的欧亚草原地带,冠以“草原”,可谓名副其实。
其次,从贸易史角度观察,草原丝路也是实至名归。茶叶、马匹、皮毛制品等固然是历史上该路段流通的大宗货物,但据史料统计,丝绸绝对是草原丝路的重要输出品。
再次,从具体交通路线来看,草原丝路是不同于“沙漠—绿洲丝路”的通道,草原丝路形成时间早于沙漠—绿洲丝路,甚至有学者认为,草原丝路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特定历史时期草原丝路与沙漠—绿洲丝路确有交集,但不能因此将二者混同。沙漠—绿洲丝路与草原丝路联络成网状,主要指6—10世纪回鹘、吐蕃与辽朝的交往。即便如此,二者因形成时间不同、主干线路有别,仍可以分开叙述,有交集联络并不意味着二者就可以合而为一。
最后,从草原丝路贸易中介者角度考虑,各个历史时期草原民族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均表明,自公元前5世纪的塞人,以及10世纪后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经与中原地区有过贸易往来。以丝绸、茶叶、马匹、皮毛为主的贸易进行的同时,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步伐也不断加速。这一切都离不开曾经活跃在草原丝路上的各民族所发挥的作用。
“草原丝路”概念具有科学性
“草原丝路”是丝路概念广义化的结果,其内涵的精准性与外延的涵盖性是衡量这一概念至关重要的方面,“草原丝路”概念的科学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概括性。“草原丝路”之称精准地体现了这一路段的主要地貌特征。草原作为此路段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观,以此地缘特征为该线路命名,一目了然,具有高度概括性。
其二,普适性。“草原丝路”是一个跨越时空、囊括古今的称谓。比起“参天可汗道”、“回鹘路”等具有时代烙印、带有鲜明民族特色,“草原丝路”这一称谓的使用更具普适性,可用于学术研究,也可用于政策宣传、旅游推广。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均能通过该名称了解草原丝路具体所指。
其三,包容性。举凡与此路相关的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都可以海纳其中,循此路线索而得以明晰。
其四,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的草原丝路有不同称谓,草原丝路是体现新时代特点的称谓,新时代要求我们创造出既能涵盖旧有称谓,又能服务于当下科研、政策宣传等多方面需求的概念,“草原丝路”体现了新时代的需求。
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丝绸之路,每一个概念外延的拓展均与时代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受并发展这些称谓,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也符合研究丝绸之路所应具有的海纳气度。正确认识“草原丝路”这一概念,厘清具体交通路线,无疑有助学术研究的推进和深入。